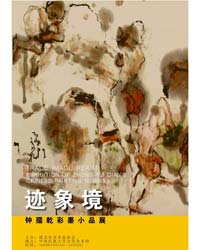大家应该注意这段话中的“标准身高”和“一般观看距离”这样的字眼。作者对观者的身体存在的意识是十分自觉的。实际上是由悬挂的玻璃片(写着文字)组成一条通向电视屏幕的视觉通道,两组视觉通道之间互成角度,从而将站在该点的观者的视线分别拉向两边。这是个极为成功的设计,其生理的不适感具有毫无例外的普通性。当然从整体上这一装置有明显的漏洞,因为视觉通道由悬挂的玻璃片组成,观众大可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总之他们没有必要一定站在作者期待的位置上去观看电视屏幕,那么成角度的双眼视觉设计就没有起作用。在上海的《以艺术的名义》装置艺术联展中,这件作品向前发展了一步,悬挂的玻璃片上成交叉状的文字条去除了,所有的文字是首尾相接的环状排列,文字的语义也首尾循环。这样视觉通道的诱导性被加强了。但文字在这里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视觉性的图案,对电视屏幕的关注与对玻璃板上的文字的阅读之间形成一对矛盾:对文字语意关注势必转移人们在屏幕上的视线。这或许是作者有意设置的又一种对正常观看方式的骚扰?
真正吸引陈劭雄兴趣的无疑是“中介”的存的在对人的影响。这一“中介”可以与康德的 “范畴” 概念或托马斯·库恩的“知识型”或“范式”之类认识论概念相称。它可以是一种视觉中介,比如你拍摄一个对象的方式,你观察一个对角的角度,也可以是一种概念中介,你理解事物的方式是有色眼镜式的,它产生偏见,制造差别以及个体的存在,如此等等。这些理性认识并不新鲜,今人惊奇的是陈劭雄能以触及身体的方式把这些思索转化为生理经验,这在中国艺术界是相当罕见的。当然,设计对身体经验的触及,要求艺术家把观众的体验,甚至观众介入的可能纳入考虑。这让我们回想 94年陈劭雄的另一件作品《改变电视频道便改变新娘的决定》。在这件录像雕塑作品中,陈在电视荧光屏上挂上各种女性化妆品,电视下方悬挂一件婚纱,二者构成一个拟人关系,电视屏幕成了新娘的头部。观众可以通过改变电视频道来改变“新娘”的形态。作品结构很简明,表面上似乎涉及了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的影响(这一特点是“大尾象”工作组的共同特征),实际上关心的已经是判断差异的问题,只是在这件早期作品中,中介的角色由电视频道的选择键来担当,还没有出现后来他的装置中的智慧成份。
在更南方的海口市,陈劭雄的朋友翁奋也在不断地从事录像艺术工作。翁奋也是画家出身。“ 90年由于对绘画的态度问题”停止绘事后,通过行为艺术的记录,从94年开始接触录像艺术。95年11月,他与女艺术家严隐鸿一起,以“变压器”工作组的名义在海口举办一个展览《男人对女人说,女人对男人说》。与陈劭雄的电视新娘相似,这里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拟人化的物品堆称,两把面对面的椅子上分别堆放安置了男性和女性的用品,外轮廓大致构成两个对称的人形。人的头部自然是由屏幕来替代,另外在地上加了一组相当的监视器,录像带的内容分别是不同的男人谈论女人与不同的女性谈论理想男性的访谈记录。有趣的是,装置的戏剧性安排是对话式的,而录像画面中人物的口吻则是自语式的。对坐的这两位电子男人和电子女人都没有谈论对方,而谈论着自己理想中的异性。
与翁奋连袂展出的严隐鸿的作品中,语言所起的作用甚至更加重要。《你又能说什么呢?》是由数十架彩电堆成的装置。每个屏幕中都有一张嘴说着什么,这些是婴儿的嘴,男人的嘴,女人嘴,教授的嘴,商人的嘴,各自发着自己的声音,相加之后成为一片噪音,作品处理问题的观念和手法都较简单。五十年代凯奇就做过结构上非常相似的噪音作品。但创作的感觉却是真切的,很明显是生存压力的宣泻,手法上也的确发挥了录像媒体的特长,因此仍然是感人的。据说二人的工作小组以“变压器”为名,本身就有在艺术中转换外界压力的寓意。这样的需求相当接近表现主义,其基础是很古典的弗洛伊德式的压抑理论。值得思考的倒是事实上存在着许多种消解和转换压力的渠道,为什么使用录像?这些压力用其他媒体能不能有效地被转换?显然在他们这里录像为口语向视觉艺术渗透大开方便大门,希望让作品说话的欲望诱使这两位艺术家选择了录像手段。
这次展览之后,严隐鸿移居北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继续关心录像,而翁奋在海南,继续对城市生活,尤其是生态环境的恶化的压力做出反应,他对录像的认识由语言扩展到音响,经常在录像带或录像装置中采用音画错位的办法来制造对比和联想,如被污染的水面图像与车流声和人声的拼贴。语言又以文字的形式进入画面,直接提示出关于“水—此前—此后”的忧患意识。
深圳的刘意 96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个展上租用了一面电视墙来展示她的《谁是我》。录像带由她的数十位朋友出镜对其进行评论,同样是把录像的可能性集中在语言的运用上。她的《结束》是做爱声为画外的音的一双女性的手洗碗的特写镜头,在短片的“结束”处,这双手将洗净的饭碗摔碎在地上。这个短片明显优于同时展出的《状态》(一个水瓶里滚动热水的特写镜头),除了音画组合的隐喻功能在此很好地将洗碗动作与女性身份加以联接外,由于摔碗的动作突兀出现,与此前单调的洗碗动作形成对比,录像的连续时间性的优势在其对过程体验的强调中得到了发挥。当然,这只是一个有效果的镜头,而一个有强度的录像艺术作品,可能应该由更多的这样的好局部来组成——虽然小品也可以“微言大义”,但媒体的可能性还为丰富,由于满足于小小的机智和简单点子,许多艺术家的工作实际上都身患隐疾。只是由于各自独立地工作,没有互通声气,甚至都不知道有其他艺术家在相似的方式上实践,这一切远远没成为明显的问题。
类似的机智小品我们在北京艺术家宋冬的作品里也经常可以看到,但是宋冬对微小细节的钟爱显然带有某种禅意体验。宋冬在北京的一次个展名为“掀开”,投影的录像画面就是作者掀开各种物品的遮盖物的特写镜头。录像成了陈述重复体验的方式,而相似体验的一再重复正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禅。这种方便创作方法论导致了宋冬录像艺术的多产,经常是一些相当平凡的生活细节的再思考,如一个被监视的人朝镜头拍照等等。这些机智有时带有社会隐喻性,如宋冬的一件装置是两个对面吵嘴的电视机,屏幕里嘴的特写分别以中文和英文的告诫对方“闭上嘴,听我说”,此类情境显然与翁奋的方法有接近之处,效果上则更为简洁。
施勇和钱喂康从 94年在上海的一系列展览中脱颖而出。不知是否一种地域传统使然,上海的装置艺术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性的“国际风格”。钱喂康的装置是以还原论为理论背景的。也就是说,他更愿意把客体描述为低水平的生理现象甚至物理现象,而不倾向于将之做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的解释。这种冷峻的还原论目光当然并不是一种简单或偏执的机械唯物主义,勿宁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相当极端的社会态度、文化态度和政治表态。钱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测量”之类的概念,正是因为还原论倾向于对客体进行量化描述。在95年电视屏幕中的形象开始进入钱喂康的测量视域,经常在屏幕形象与其原型之间进行并置,其实这时“测量”已经更多呈现为一种心理行为了。与钱喂康相比,施勇稍具人文气息。虽然他的作品同样经常具有方整简洁的外形、平滑的表面和过程性的变化因素,但他的用材常常可以引申出一种隐喻性。如他对相纸和音响的处理,实际上基于他对大众传媒的态度。这种兴趣使之一直与电子媒体若即若离。
94年在上海的文献展中播出作品《被注视的睡眠——十二个人的睡相》之后,佟飚从浙江美院毕业进入一家电脑公司搞设计工作。社会工作的经验使他的兴趣转移到人际关系的主题上,这时摄像机的镜头就成了他表达对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态度的手段,而他独特的表达方式在于直接用镜头去代替肉身,在镜头与他人的身体之间构造关系。关于作品《触及》(1995),佟飚有一段诗意的描述:
“肉体的频繁接触即使在同性之间也正变得无可非议。然而一种紧张而隐蔽的接触也正透明于公共生活之中,肉体的日益亲密却使个人之间的社会距离逐渐延长,对他人的占有欲和伤害性司空见惯的存在于各个角落。”
《触及》的操作方式是作者将摄像机背在背部,镜头朝后,一个助手在背后追赶拍摄者,并一直伸出手去试图擒获拍摄者,拍摄者则尽力奔跑逃脱追赶者。触及他人身体的努力开始于一座迷宫,然后依次是公园、人行天桥和商场——越来越杂乱不堪的环境。于是出现在镜头里的是因为奔跑的颠簸而晃动的场景,不时闯入镜头的追赶者的形象和他伸向镜头的抓人的手掌。环境背景声被抹去了,只留下奔跑者急促的喘气声,从而使整个五分钟长的录像带有一种梦境般的非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