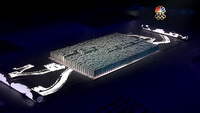中国的文化复兴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只有一字之差,似乎可以相提并论。其实不然。西方的文艺复兴,会让你想到一本精美的大画册,那一时期文化艺术的杰作美不胜收,即使你不了解它们对于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巨大作用,也照样可以欣赏。因为人家早已翻过历史的一页,留下的都是精品。
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则一直处于变革的阵痛当中。所以,提起中国的文化复兴,总会让你想到一张大圆桌,旁边围满了方方面面的人物,提出形形色色的看法和意见,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还是文艺论争、思想动态、时局走向,都可以装进文化的这个大篮子里来交换,都与中国的复兴扯得上些关系。这更像是处在争论不休的春秋战国时代,而不是像米开朗基罗那样多少年如一日地蹲在教堂里默默创作他的雕塑,尝试新的理念,不经意间推动了社会进步,成为文艺复兴一代宗师。
不过,这也并不奇怪。西方文艺复兴相对比较单纯,它源于一个新兴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时代诉求,他们新的精神理想也开创了文化灿烂的新天地。中国文化复兴则是起自于一个古老民族渴望重新崛起的历史愿望,而且这一历史进程仍在复杂演进之中,所以其现实政治的意味也必然很浓,是一个非常宽泛、模糊不清的概念,甚至与黄仁宇提出的中国“大历史”概念有些相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探讨中国的文化复兴,也是在探讨中国的前进道路;我们为文化复兴献策,也就是为民族强盛立言;圆桌的气氛既像是百家争鸣,也像是指点江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近现代中国在社会理想追求上的重大转向非常值得重视,应当视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最重要的迹象。因为“复兴”的真正含义显然不是要恢复古代的辉煌,而是要激发现代的创造性力量。西方的文艺复兴尚且如此,中国的文化复兴就更是如此,而且它不再借用古人的衣裳和旗帜,甚至试图割断与传统的联系,走上一条与千年历史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一重大转折自1840年开始,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达到高潮。
1978年,北京红旗越剧团导演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
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生活和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其发展之快、变化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不仅令世人惊愕,连中国人自己也惊讶。不管你是持何种看法和评价,这一事实有目共睹。考虑到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变化,而是占世界人口1/5人类的生活巨变,其影响之深远,内力之深沉,其背后的文化动因就不可不深思了。这就像火山爆发,不管是福是祸,当看到岩浆剧烈喷涌时,你都会惊异于其内部力量的神秘和伟大。
特别是,面对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持续快速变化,人们不仅要问:一个长期停滞的文明古国为什么能够爆发出惊人活力?而且更要问,为什么这个社会虽然看起来已经被不断的变化拖得溃不成军、踉踉跄跄、略显狼狈,却仍然没有真正停下脚步的意思,整个社会要求刹车的呼声并不强烈。结果,一方面是问题成堆,摁下葫芦浮起瓢,一方面却是人们似乎仍然愿意承受、容纳和尽力消化问题。“北京共识”首倡者乔舒亚即注意到,在2002年中国党代会上,党的领袖在90分钟讲话里用了90次“新”字。而曾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中国农民,每过三年就会完全淘汰他们所用的种子。所以他问,为什么同样的意识形态,面临同样的问题,苏联最后的反应像是一具植物人,而中国则像患上了多动症,他们似乎是在利用创新来减少摩擦损失,因为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那么中国这种独特的适应能力和变革的动因是什么呢?
有关中国历史延续性问题,并不是现在才引起人们兴趣的。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独一无二的持久生存能力。他们非常好奇的是,为什么别的国家往往表现为文明的盛衰,一蹶不振,中国文明却表现为朝代的更替,一旦改朝换代,马上衰而又兴,东山再起。譬如东、西罗马分裂就永远地分裂了。而几乎同时,中国在历经几百年分裂后却又在隋唐时代重新统一了,而且更强大、更有活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19世纪的黑格尔时代似乎找到了答案,就是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某种历史活化石,一个没有真正向上演进历史的国家,因为封闭而幸存,因为停滞而永存,一旦遇到外界新鲜空气,就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1984年,中央美院等10所艺术院校于《北京晚报》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模特儿,冲破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的束缚。
但今天看来,这个看法失之片面,中国的延续性有时像是死而不僵,有时又像是凤凰涅。四大古国幸存其一,一个民族能够不间断地延续数千年,从土里刨出来的殷商甲骨文汉字现在还在使用,而且是同一群人在用,而不像亚述人的古楔形文字早已成为遗迹,这其间必有道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曾经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他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部分地具有“改革的能力”,能够“通过重新树立其理想”,使这个古老国家生存下来。也就是说,看似守旧的中国文化传统其实有革故鼎新的一面,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这个文化基因,只待合适的时机生根发芽了。
1983年,继自行车普及之后,摩托车被引入中国,一时间成为家庭富裕的象征。
我认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确在重新树立其社会理想追求,从而体现出中国式文化复兴的最重要特点。概括来说就是:百年来的中国在其生存和发展模式上已经更换了新的文化发动机,即从那种周而复始的农业社会的圆形封闭轨道,已经转向了“历史直线进展”的开放式的理想追求。这一转变的契机当然就是东西方文明的迎头相撞,以及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
1982年,“个体户”这一群体得到正式承认。
千百年来,适应着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华民族本来已经成功发明出一套循环往复的生活模式及静态化的社会理想,这就是年年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讲的最多的也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如果不是外界因素,可以年复一年,千年不变。
但是今天,经过千年未有的那场“大变局”,中国社会的一切都变了,一种求新、求变的陌生理想已经深入人心,主导着今天的社会生活。你看今天中国人唱的歌曲,几乎每首歌的末尾都是盼望“明天会更好”、“明天生活比蜜甜”。甚至连小学生写作文,也是按照这种“直线进展”的思维方式去畅想和企盼,这几乎已经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种陈词滥调,但这样的理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诗文中却一点也找不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社会理想追求的确已经历史性地发生变化,不可逆转地从静态转向动态、从循环转向直线,而如今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它合乎逻辑的演进,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某种重大体现。
中国社会理想追求这一重大转向的实质,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学术性的语言来阐释就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问题就在于从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国家。”不如此,传统农业社会的单纯结构就无力应付现代世界的复杂生活,就不能摆脱落后屈辱地位。和平时期不能支持大规模现代工业的建设,战争期间不能全方位高效动员来支撑战时体制。也就是说,要救亡图存,就得求新,求别,跟上时代潮流。
但从静到动、从循环到直线,社会理想追求的这一重大转向对古老的中国来说是多么艰难,需要决绝的精神,这就见出了闻一多的意义。闻一多与屈原的行为、气质相近,为什么他们代表两个时代呢?就因为屈原殉的是士大夫阶层的传统理想,而闻一多殉的则是“明天会更好”的陌生理想,是求新、求变的新的时代要求。所以,当闻一多1944年看到国家领袖蒋介石出版的新书《中国的命运》了无新意,甚至还想用儒家那一套进行统治时,他就大惊,大怒,最后拍案而起,以死相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闻一多是第一个以献身激情把民族进步的要求变成一种非凡的使命、为民族生存提供新的精神资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然,这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倾向于断绝传统,甚至提出“全盘西化”主张,但实际上,这是因为危机太深重了,应战太艰难了,因而需要壮士断腕般的魄力和意志,实际上仍然与精神传统的血脉相连。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佩霞就关注过这一问题,她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人在每一时代都运用了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去确定目标,回应挑战,保卫自己,增强力量。因为一代人的行为对下一代人继承的资源将会产生影响,所以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变化又是与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确信无疑”。费正清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认为,中国的传统儒生与现代儒生是有一脉相承之处的,即“中国的优秀分子一代接一代地努力应付从帝国时代晚期继承下来的国内问题,回答工业化的西方提出的历史悠久的挑战,这种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理想追求的重大转向并非是中国文明的瓦解,“全盘西化”的实现,而是挑战与应战的历史结果。危机越严重,转向越彻底,变化也越惊人。
今天,中国社会唯一不变的现象可以说就是不断变化本身,中国人似乎已经颇能适应这种变化的过山车式的节奏,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少见的。中国文化复兴所催生的这种曾经长久沉睡的力量如此巨大一点也不奇怪。考虑到中国的独特精神特质,诸如不重彼岸世界,看重实用理性精神,有愚公移山式的吃苦耐劳精神等,一旦注入新的理想动力,它所释放的能量就将不同凡响。1896年发表的一篇美国记者的文章非常有预见性,他指出:“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中国工业竞争的危险程度,是其他任何一国都不可比拟的⋯⋯有人对此表示某些怀疑。难道2000年的中国佬不会跟我们今天熟悉的中国佬一模一样吗?”但是,这位美国人的回答正是基于中国人的文化特性上的:“我们并不是通过古代文献来评价现代的中国,而是通过她现在的生活。了解中国的人也知道,中国人的保守思想并未延伸到那些有关贸易、工业、商业或投机买卖的活动领域。它只是在信仰、伦理和风俗方面具有保守思想,与商业毫不相干。”也就是说,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现世生活热情和能量,一旦再认可了西方人的直线式理想追求,也想在这条跑道上比试一下的话,就将搅动世界。
1992年,深圳8•10股票风波,中国人在信仰、伦理、道德方面的保守并不妨碍他们在商业和生活上的热情和追求。
仿佛是作为注解,前两年有一部名为《输家赢家》的德国纪录片在海外到处获奖,就是因为它难得地把镜头切入到去德国鲁尔区拆运一座破产的现代化焦化厂的四百名中国工人当中。德国女导演是当地人,对德国工人的失落感感同身受,也对中国人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所以以第一手资料展现了中国人古老的生存动力和乐天派精神。中国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每个月挣400欧元,干着德国工人给4000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德国人以为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国工人一年半就完成了。他们把每一点钱攒下来的理想和坚忍,只是为了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下辈子别再做工人。他们中每个月有7人会喜滋滋地被选为“最佳工人”,戴上大红花照像,当然也只有这种奖励,但他们乐观、满足、任劳任怨,也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的发展速度究竟为何而来,引起西方人的震惊。
我并不想无条件地赞扬这一新的社会理想追求给中国带来的崭新面貌,因为这一转变过程本身充满了太多的痛苦,也是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巨大撕裂,但又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我在此只想指出: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迎接一个个接踵而至的陌生挑战,它是有潜力、有智慧能够把不同时代的经验教训不断变成新的传统,甚至在最危机时刻,壮士断腕,决然转向的。如果看不清这一点,就很难深入探讨中国今天的文化复兴问题。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口号,充分展现“绿色”、“科技”、“人文”观念,以主体形式输出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
当然,地球只有一个,而且越来越像一个不大的村庄,如果人类都无限制地求新、求变,想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获取更多的东西,那么地球如何负担?环境保护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又怎样协调?这的确是一个新的问题。但应强调的是,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人类的问题。它原本由西方历史文化中催生出来,现在则需要由全体地球人一起来解决,转变既往的生活方式和理想诉求,共同构建一个真正文明与和谐的世界。